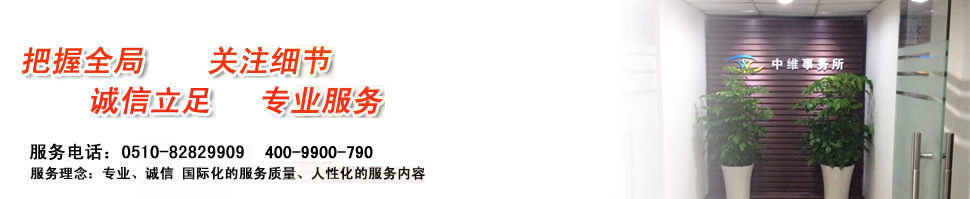废除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要求与交易安全保障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是法律为公司资本设定的一道底线,它是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立法者期望通过这一底线设置为公司清偿能力提供担保。但这一期望不仅未能有效实现,而且使得许多弱小投资者无法利用公司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开展商业活动。譬如,对于设立一家普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而言,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要求的1000万元的最低资本金,还是2005年《公司法》要求的500万元的最低资本金,都超过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又如,2005年《公司法》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本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满足弱小投资者的需求,但却规定了10万元的最低资本金,违背了法律承认一人公司的真义。
废除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要求,公司的注册资本相应地体现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或者认购的出资总额或者股本总额。废除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要求,并非不需要注册资本,而是对于设立公司到底需要多少资本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再强行干预。譬如,根据2005年《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3万元人民币,似乎很低。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它依然受制于法律管制,而不是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投资。在废除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要求的情况下,有人担心容易出现“皮包公司”(如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名义资本”或者出现“一元钱公司”)并引发公司欺诈,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投资者根据公司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投入的必要启动资金。如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数额较大,股东或者发起人就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也就较大;如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数额较小,股东或者发起人只需投入较少资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就较小。如果公司设立时暂时无须投入资金,股东或者发起人仅仅为了设立公司而投入名义资本金或者“一元钱”资本金,“白手起家”也无不妥。尤其是对于刚开始创业的弱小群体而言,最低注册资本限额要求的废除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情感激励。退一步讲,即使有些投资者利用法律提供的这种制度优惠意图从事欺诈活动,也是一个可由市场机制自身解决的问题。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示的,为公众知晓,交易相对人在明知交易对手资本羸弱的情形下自然应当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是否与之发生交易。很显然,法律代替不了当事人,政府无力包揽市场交易。
公司的注册资本对于公司的清偿能力确实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问题是,传统法律对公司资本这一作用的认识存在一定误解,并夸大了这一作用。公司的注册资本在登记意义上是一种静止的概念,它仅仅在法律观念上存在。公司一旦成立,注册资本即转换为公司资产,公司资产是动态的,它将随着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展开而发生变化。如果公司经营管理得法,公司资产就会增加;如果公司发生亏损,公司资产就会减少。然而,公司的注册资本却始终保持不变,除非公司再次通过法定程序增加或者减少资本。
公司资产才是公司清偿能力的真正体现。法律应该关注的是公司资产问题,即应关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保障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果法律仅仅着眼于公司资本,不仅不能保障公司的清偿能力,反而会增加公司设立负担。公司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采取措施保障公司资产和交易安全。譬如强化公司治理,在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包括关联交易制度、大股东和实际控人制度、重大资产处置制度、内部审计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保障公司遵守正常的运作和决策程式;股东应当正当行使权利,如果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或者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股东应当对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债权人承担责任;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等。
应当注意的是,2013年修正的《公司法》取消了对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管制,仅仅针对的是从事普通业务的商事公司而言,并不包括从事特殊业务的公司,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从事其他须经特别许可业务的机构,法律并未取消对这类公司或者机构的资本管制。这是因为,这类公司或者机构所从事的业务可能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可能涉及自然资源统筹调配,可能涉及国家公共安全,因而法律必须介入并需要对之施加必要的管制,各国法制概莫如此。
|